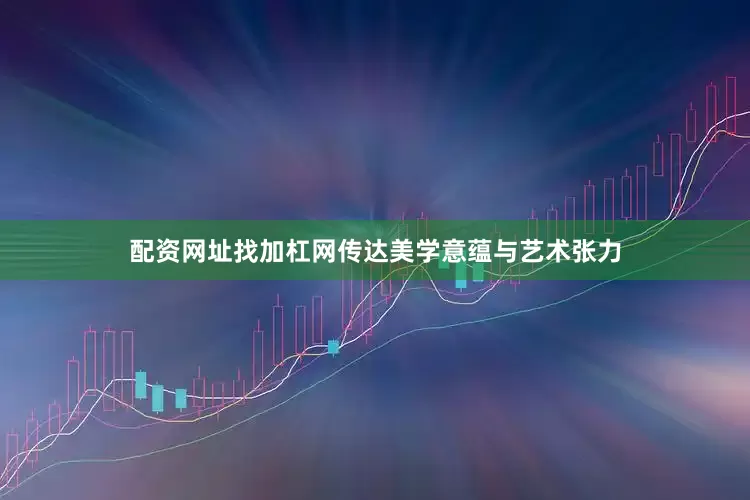我是广州人,去了趟景德镇,三个问题盘了三天,本地朋友能给说道说道不?
广州的茶餐厅永远锃亮,奶茶拉花要对称,烧腊斩件得码成菱形——精致是刻在DNA里的。可景德镇这“瓷都”,走在街上像掉进了釉料缸,青的、白的、开片的瓷片嵌在墙缝里,连路灯杆都裹着窑变釉色,逛了三天,脑子里的问号比瓷器上的冰裂纹还密。
瓷片当石头铺街,为什么对“土与火”痴迷到骨子里?
在广州,餐具是超市货架上的流水线产品,好看就行;到了景德镇,连菜市场阿姨的菜篮子都带着故事——竹筐里垫着块碎青花,“这是老厂出的,防磕!”
凌晨五点的陶艺街比早茶市还热闹。穿围裙的师傅蹲在地上揉泥,高岭土在手里翻卷,“要揉够三百下,气泡才跑干净”,额头上的汗滴进泥里,他眼皮都不抬。我指着块灰扑扑的土问价,老板眼睛一瞪:“这是釉果,比你喝的普洱金贵!”
展开剩余83%更绝的是巷子里的“瓷痴”。路过一户人家,窗台摆着十几个茶杯,个个歪歪扭扭,主人阿婆却宝贝得很:“这个是柴烧的,火痕在这儿;那个是电窑的,釉色亮——机器做的?那叫杯子,不叫瓷。”
广州人家里的碗碟坏了就扔,景德镇朋友却有个“锔瓷盒”,碎了的盘子用铜钉拼起来,“你看这裂纹,比新的还耐看”。连街边的花坛都用碎瓷片拼出牡丹,老板说:“土烧的瓷,碎了也得回土里去,不浪费。”
疑问:天天跟泥巴、火打交道,手上全是釉料渍,就不嫌麻烦?这份执着是从高岭土里长出来的?
手艺人拉坯像打坐,吵架却为“釉色差半分”?
广州人做生意讲究“和为贵”,买东西问价,老板会说“靓仔喜欢就少点啦”;景德镇的手艺人却像带刺的青花,温柔里藏着硬气。
在工作室看师傅拉坯,转盘转得慢悠悠,他手指轻按慢推,泥巴像有了魂,半个钟头才出个碗坯,大气都不喘。可隔壁摊位的两个师傅吵起来了,“你这郎红太暗,肯定是窑温差了五度!”“你懂个屁,我这是仿古釉!”声音比拉坯机还响,末了却互相递烟:“下午开窑,过来看看?”
我想买个茶杯当伴手礼,问能不能刻字,师傅头也不抬:“字丑了毁釉色,不刻。”转头却拿出个试釉的小瓷片:“这个送你,比刻字实在。”
广州的网红店讲究“打卡感”,景德镇的老窑口却藏在巷子里,门楣上就写“老王烧瓷”。推门进去,地上堆着废坯,老王正用砂纸磨碗底,“去年的货有瑕疵,磨平了再卖,不能砸招牌”。
疑问:拉坯时能坐一天不动,争起手艺来却像炸窑,这脾气是被窑火烤出来的?
吃饭用的碗比菜还“抢戏”,瓷味怎么比辣味还重?
广州人吃饭,餐具要“衬菜”,白瓷盘装烧腊,玻璃碗盛艇仔粥;到了景德镇,菜还没上桌,先被碗碟勾了魂。
早餐摊的冷粉装在粗陶碗里,碗沿带着手指捏过的痕迹,老板说:“这碗吸油,粉才不腻。”我夹粉时碰了下碗,居然是温的——“刚从窑里取出来的,捂手”。
朋友带我吃瓷泥煨鸡,砂锅是本地陶土做的,鸡埋在窑渣里焖,掀开盖子,砂锅里的油星溅在瓷桌上,印出点点油花。“这桌子是淘汰的窑板改的,不怕烫”,他边说边用瓷勺敲了敲,“听听,这声儿脆不脆?”
最绝的是茶摊。老板用个带开片的砂壶泡茶,倒在小瓷杯里,杯底刻着“光绪年仿”。“假的?”我惊了。他哈哈大笑:“仿的是手艺,又不是骗你钱——咱景德镇人,玩的是瓷,不是古董。”
广州的糖水要精致摆盘,景德镇的甜汤却装在豁口的老瓷碗里,“这碗盛了三十年甜汤,比糖还入味”。连酱油碟都是碎瓷拼的,老板得意:“咱吃的不是菜,是过日子的瓷气。”
疑问:用破碗吃饭不硌嘴吗?这瓷里瓷气的饮食,是怕日子没“釉色”?
总结:景德镇的“窑火哲学”
在景德镇待了三天,算明白为啥说“白如玉、明如镜、薄如纸、声如磬”了——这里的瓷,早不是摆件,是日子本身。
● 土是根——揉泥的力道里,藏着对“万物归土”的认,再金贵的瓷,说到底也是高岭土烧的。
● 火是魂——争釉色、较窑温,不是较真,是怕对不起那把火,毕竟土成瓷,全靠火炼。
● 破是韵——碎瓷能铺路,豁碗能盛汤,就像这里的人,不端着,把不完美活成了味道。
临走前还是没琢磨透:为啥景德镇人守着窑口,能把泥巴烧成“白金子”,却连个早餐碗都舍不得换个新的?有本地老乡给解解惑不?
发布于:四川省广东股票配资开户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